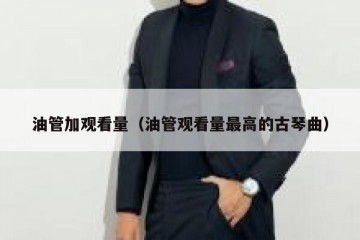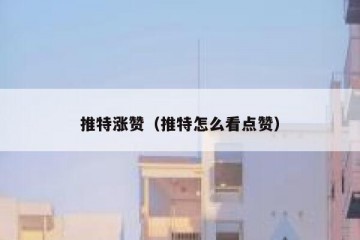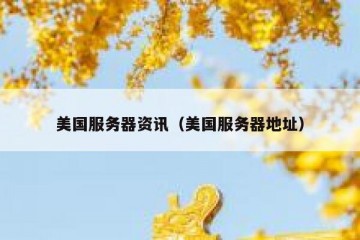facebook新闻(facebook新闻标签)
2018-01-05英语新闻一则The next frontier Using thought to control machines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may change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使用浏览器扫码进入在线客服窗口)
复制联系方式
TECHNOLOGIES are often billed as transformative. For William Kochevar, the term is justified. Mr Kochevar is paralysed below the shoulders after a cycling accident, yet has managed to feed himself by his own hand. This remarkable feat is partly thanks to electrodes, implanted in his right arm, which stimulate muscles. But the real magic lies higher up. Mr Kochevar can control his arm using the power of thought. His intention to move is reflected in neural activity in his motor cortex; these signals are detected by implants in his brain and processed into commands to activate the electrodes in his arms.
An ability to decode thought in this way may sound like science fiction. But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BCIs) like the BrainGate system used by Mr Kochevar provide evidence that mind-control can work. Researchers are able to tell what words and images people have heard and seen from neural activity alone.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encoded and used to stimulate the brain. Over 300,000 people have cochlear implants, which help them to hear by converting sound into electrical signals and sending them into the brain. Scientists have “injected” data into monkeys’ heads, instructing them to perform actions via electrical pulses.
As our Technology Quarterly in this issue explains, the pace of research into BCIs and the scale of its ambition are increasing. Both America’s armed forces and Silicon Valley are starting to focus on the brain. Facebook dreams of thought-to-text typing. Kernel, a startup, has $100m to spend on neurotechnology. Elon Musk has formed a firm called Neuralink; he thinks that, if humanity is to survive the adv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needs an upgrade. Entrepreneurs envisage a world in which people can communicate telepathically,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machines, or acquire superhuman abilities, such as hearing at very high frequencies.
These powers, if they ever materialise, are decades away. But well before then, BCIs could open the door to remarkable new applications. Imagine stimulating the visual cortex to help the blind, forging new neural connections in stroke victims or monitoring the brain for signs of depression. By turning the firing of neurons into a resource to be harnessed, BCIs may change the idea of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That thinking feeling
Sceptics scoff. Taking medical BCIs out of the lab into clinical practice has proved very difficult. The BrainGate system used by Mr Kochevar was developed more than ten years ago, but only a handful of people have tried it out. Turning implants into consumer products is even harder to imagine. The path to the mainstream is blocked by three formidable barriers—technological, scientific and commercial.
Start with technology. Non-invasive techniques like an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struggle to pick up high-resolution brain signals through intervening layers of skin, bone and membrane. Some advances are being made—on EEG caps that can be used to play virtual-reality games or control industrial robots using thought alone. But for the time being at least, the most ambitious applications require implants that can interact directly with neurons. And existing devices have lots of drawbacks. They involve wires that pass through the skull; they provoke immune responses; they communicate with only a few hundred of the 85bn neurons in the human brain. But that could soon change. Helped by advances in miniaturisation and increased computing power, efforts are under way to make safe, wireless implants that can communicate wi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neurons. Some of these interpret the brain’s electrical signals; others experiment with light, magnetism and ultrasound.
Clear the technological barrier, and another one looms. The brain is still a foreign country. Scientists know little about how exactly it work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complex functions like memory formation. Research is more advanced in animals, but experiments on humans are hard. Yet, even today, some parts of the brain, like the motor cortex, are better understood. Nor is complete knowledge always needed. Machine learning can recognise patterns of neural activity; the brain itself gets the hang of controlling BCIS with extraordinary ease. And neurotechnology will reveal more of the brain’s secrets.
Like a hole in the head
The third obstacle comprises the practical barriers to commercialisation. It takes time, money and expertise to get medical devices approved. And consumer applications will take off only if they perform a function people find useful. Some of the applications for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are unnecessary—a good voice-assistant is a simpler way to type without fingers than a brain implant, for example. The idea of consumers clamouring for craniotomies also seems far-fetched. Yet brain implants are already an established treatment for some conditions. Around 150,000 people receive deep-brain stimulation via electrodes to help them control Parkinson’s disease. Elective surgery can become routine, as laser-eye procedures show.
All of which suggests that a route to the future imagined by the neurotech pioneers is arduous but achievable. When human ingenuity is applied to a problem, however hard, it is unwise to bet against it. Within a few years, improved technologies may be opening up new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brain. Many of the first applications hold out unambiguous promise—of movement and senses restored. But as uses move to the augmentation of abilities, whether for military purposes or among consumers, a host of concerns will arise. Privacy is an obvious one: the refuge of an inner voice may disappear. Security is another: if a brain can be reached on the internet, it can also be hacked. Inequality is a third: access to superhuman cognitive abilities could be beyond all except a self-perpetuating elite. Ethicists are already starting to grapple with questions of identity and agency that arise when a machine is in the neural loop.
These questions are not urgent. But the bigger story is that neither are they the realm of pure fantasy. Technology changes the way people live. Beneath the skull lies the next frontier.

流言终结者 三人组为什么要离开? 卡丽·拜伦 ,托利贝勒西,格兰特·今原
这个似乎并没有十分具体的原因,但是据亚当和杰米在 comic con 2014上的说法,他们认为mybuster这个节目已经偏离了它一开始的目标,他们希望让节目重新回到最初的时候--也就是只有亚当和杰米的时间。格兰特·今原和托利·贝勒西则在Facebook上发消息称在他们离开后,“节目将走向一个新的方向”(“the show is taking a new direction”),而现在对于他们而言,将会是开始“一场新的冒险”(“the next adventure”)
关于亚当和杰米在comic con上发言的相关探讨(原视频只在YouTube上有):
关于这个的Facebook截图和新闻解释链接:
(如果上面的无法显示:)
【其实理由很牵强,但他们不愿意说的很具体】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脸书第一夫人”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不仅值得推荐给女性
谢丽尔 桑德伯格,1969年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一个犹太人家庭,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哈佛商学院MBA学位,曾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办公厅主任、谷歌全球在线销售和运营部门副总裁,在2008年Facebook仅有550名员工时(谷歌当时有2万多名员工)被扎克伯格挖到Facebook任首席运营官至今,被称为“Facebook的第一夫人”。
2013年她出版了《向前一步》一书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2014年的新版中,增加了很多案例,包括很多因为读了她的书采取行动改变生活的女性的自述。
在《向前一步》的导言里,桑德伯格写道“这本书不是一本回忆录,尽管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故事;它不是一本励志自助书,尽管我真心希望它能够帮助读者;它也不是一本关于职业生涯管理的书,尽管我在书中提出了一些这方面的建议。它更不是一部女性主义宣言……好吧,它有点像,但 我希望它不仅能够激励女性,同时也能激励男性。 不管这是本什么样的书,我都想 写给那些希望进入高级管理层或是竭力追求自己人生目标的女性 ,不论她们处于怎样的事业阶段——刚刚起步,或是暂时休息但也许某天还会重返职场。我也想写给那些 想要理解周围女性(女同事、妻子或是姐妹)所面临的困难、愿意为推动世界平等贡献力量的男性 。”
桑德伯格指出,“所有人,包括我在内,不管我们承认与否,都是带有成见的。假设我们都能做到客观,这实际上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产生 社会 学家所说的“偏见盲点”(bias blind spot)。这种盲点将导致人们对自己的客观立场过分自信,使得他们无法克服偏见带来的影响。”
性别偏见(或说歧视)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偏见。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中有一名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各种偏见不仅影响男性,更塑造女性自身。性别偏见潜移默化到你几乎不能注意到那是偏见,而认为理应如此。
《向前一步》里面写的美国的所有两性问题现象,中国几乎都一样,从过去到现在。比如“大萧条时期,我的外祖母被迫从高中退学,开始帮着维持一家老少的生计。 在当时的 社会 ,没人会让男孩辍学,一个家庭若要提高 社会 、经济地位,希望就寄托在家里男孩的教育上。 而女孩因为不会对家庭的经济收入有太多贡献,所以能体面持家就可以,受不受教育根本不重要。”女性“ 职业抱负与个人发展的结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富有挑战性 。几乎是在同样的人生阶段,我们既被要求在工作时间上要有最大投入,生理上又要求我们生儿育女。丈夫们通常不分担家务,也不帮着照看孩子,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同时承担着两份全职工作。此外,工作条件也没有改善到可以为我们提供兼顾家庭所必需的弹性时间。”“男性的成功不仅会被绝对的数字来衡量,而且还常被拿来和他们的妻子作比较。 在对幸福婚姻形象的描述中,丈夫的事业常常比妻子的事业更成功。如果情况刚好相反,他们的婚姻就会被认为受到了威胁 。”
桑德伯格写的女性的这些特征,我和我身边的女性也大多如此。“ 女性对自身表现的评价普遍低于实际情况,而男性则会过高地评价自己的表现 。”“以我的经验而言,女性对于角色变化、寻求新的挑战则更为谨慎。我常常发现自己总是在试图说服她们进入新的领域工作。我已经和女性员工有过多次谈话,她们对我的鼓励通常作此回应:‘我在这方面可能不是很擅长’,‘这项新工作听上去很令人兴奋,但我没有类似的工作经验’,或‘现在的工作中我还有许多要学习的’。印象中我似乎从没与男员工有过这样的对话。”
桑德伯格自身的一个例子很有意思:
“ 即使是现在,我还远称不上能够自如地表现出自信 。在2011年8月,福布斯公布了该年度‘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我很清楚,自己位列其中并不是科学公式计算的结果,杂志喜欢制造排行榜是因为当读者点击每个人物的名字时,都会产生很大的页面浏览量。不过,我很吃惊地——准确地说是吓坏了,发现我位列这个排行榜的第5名,居然排在米歇尔·奥巴马和索尼娅·甘地的前面,这太荒谬了。
我真没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反倒感觉被暴露在公众视野里,很是窘迫。当脸谱网的同事在办公楼里拦住我大加称赞时,我告诉他们这个排行榜是‘可笑的’。当朋友们在脸谱网上发布新闻链接时,我请他们删掉帖子。几天后,长期担任我的执行助理的卡米尔·哈特告诉我,我对福布斯排行榜这件事处理得很差劲,我应该立即停止与那些提起福布斯排行榜的人争论‘为什么这件事是荒谬可笑的’。我在太多人面前表现出了自己的不自在和不安全感,其实,我只需要说声‘谢谢’就可以了。
我怀疑,一个男人会不会因为感到自己越来越有影响力而不知所措。我知道,我的成功来自于勤奋的工作、他人的帮助以及在正确的时间站在了正确的地方。同时,我也知道, 为了继续成长、挑战自我,我必须要相信自身的能力。我仍然要面对那些超出我资历的事情 ;我仍然会偶尔感觉自己像个“骗子”;我也仍然会时不时地发现自己在谈话中被忽略、不受重视—— 而我身边的男士们却不会有这些想法 。好在我终于知道应该深吸一口气,仍然让自己的手高举着。我已经学会了往桌前坐。”
很有同感。即使我从小学习成绩优异,热爱学习,努力工作,被别人夸赞的时候,我还经常觉得别人高估我了。我也早就注意到男同学、男同事们通常比我更自信、更进取。
书中列举了很多数据,从在校学习成绩来看,女性完全不弱于甚至略优于男性。但越高级的职位女性比例越低。书中写道“在全世界范围内,企业领导层的女性比例就更低了。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里仅有4%是女性。在美国,企业主管人员和董事会中女性分别约占14%和17%,十多年来这个比例都没有什么变化。在中国主要的上市公司里,企业董事会中的女性占8.5%,而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女性不到4%。”这里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里仅有4%是女性,是2012年的统计。到2017年,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里有32名是女性,也就是占6.4%。
“这本书充分支持积极进取的女性,支持雄心勃勃地追求自己人生目标的女性。我相信 增加拥有权力的女性数量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必要元素,但我并不认为成功或幸福只有一种定义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事业,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孩子,也不是所有的女人两者都想要。我从不主张我们应该拥有同样的目标。许多女性没有兴趣追求权力,不是因为她们缺乏进取心,而是因为她们已经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多人之所以能够做出一些对世界有重要贡献的事,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爱。我们必须详细地规划自己独特的人生航线,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梦想制定恰当的目标。”
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可以不同,但都需要付出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桑德伯格对女性从职业到婚姻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
工作方面:“女性回避拓展性工作、不愿担任领导者角色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们过于担心自己不具备承担新任务所需要的技能。这完全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任何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能力。惠普公司内部的一项报告揭示,女性只有在认为自己100%符合条件的时候才会公开申请职位,但男性只要觉得自己有60%的条件符合就会对工作邀约做出回应。这个差异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 女性需要转变思路,不要总说‘我还没准备好’,而要去想‘我想做,而且我可以边做边学’。” 作为全职妈妈,不要相信“全能女人”的神话,试图做到一切还期待做得超级完美。“ 完成,好过完美。 ”只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力求完美。
婚姻方面:“对于一个正在寻找人生伴侣的女性,我的建议是,她可以和各种类型的男人约会:坏坏的,酷酷的,有承诺恐惧症的,以及满怀激情的,但别和他们结婚。坏男人性感的因素不会让他们成为好丈夫。到了想安顿下来的时候, 你应该找一个愿意和你平等相处的男人。 这类男性会认为女人应该聪明、有主见、有事业心;他会重视公平,并做好分担家庭责任的准备,甚至非常乐意这么做。这样的男人的确存在,请相信我,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他才是最性感的。”
男性看了这本书,可以更好地理解、支持家人(母亲、妻子、女儿,特别是妻子)、女同事(上级、同级和下级),获得更美满和谐的家庭以及更好的工作环境。书里援引了一些研究,“伴侣之间的平等关系会让双方更快乐。丈夫多做家务,妻子就不会那么抑郁,两人的冲突也会减少,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自然会提高。当女性在外工作,分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时,夫妻关系也更稳固。 对于男性,更多参与孩子的养育过程也能够培养自己的耐心、同情心和适应能力,这些特质对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对于女性,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在家庭事务上的决策能力,即便遭遇离婚也能保护自己。此外,收入的增加还是未来生活重要的安全保障,因为女性的寿命一般比男性长。”
看到男性参与孩子养育的好处,想起微软CEO纳德拉,他的儿子出生时由于宫内窒息,患有重度大脑性瘫痪。但是他将这一人生经历转化为财富。“ 身为一位有同理心 (Empathy,或译为共情) 的父亲,加上探究事物核心和灵魂的渴望,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领导者 。我希望将同理心置于我所追求的一切的中心——从我们发布的产品到新进入的市场,再到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男女平等问题特别需要男性的理解和支持。桑德伯格指出,“由于大多数管理人员都是男性,我们还需要让他们能够自如地跟女性员工直接提出这些问题。”“在一位女性拥有支持她的雇主和同事、家里有分担家庭责任的伴侣之前,她们很难做出真正的选择。在一位顾家的男性赢得舆论完全的尊重前,他们很难做出真正的选择。”
公司等各类组织都可以采取行动推动男女平等。书中写了一个例子,“仅仅是公开地谈论行为模式,就会让潜意识行为成为有意识的行动。比如,谷歌有一个鼓励工程师毛遂自荐、争取升职的特别机制。公司发现男员工比女员工行动更积极,于是谷歌管理团队与女员工公开分享了这方面的数据,随后,女员工毛遂自荐的比例显著提高,几乎和男员工持平。”
原来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的性别平等在全球还不错,特别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从 社会 观念意识上,对女性还有很多传统偏见;在推进男女平权方面的主动性和发达国家有差距,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 社会 发展阶段还没到那个程度,但也有观念意识的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并有意识地推动解决)。很多国家为推动性别平等采取了不少措施,如一些国家规定了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比例下限,一些公司规定招聘的女员工不得低于一定比例,甚至不能歧视女性成为“政治正确”的问题之一(桑德伯格认为,美国有的公司对避免性别歧视做过了头,以致管理者都不敢问女员工结婚了吗、有孩子吗或生育计划,其实有时是出于善意)。而中国几乎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我注意过, 欧美大银行年报中,很多会提到本行在员工包容性和多样性(包括性别、种族、性取向等方面的平等)方面的成就,而中国的银行年报中几乎不会提到这个问题。 如汇丰控股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中写道“我们在平衡领导层性别比例方面取得进展,但亦承认有改善的需要。2018年,我们参与30% Club运动 承诺在2020年前达致30%高级领导层成员 (环球职级架构中属0至3级的雇员) 为女性的目标 。为达到这个进取的目标,我们订下指标,以期在2018年底前有超过27.6%的高级领导层成员为女性。当前比例已达到28.2%。”从汇丰公布的全公司性别情况统计可以看到,女性员工占52%,男性员工占48%,但在管理层中,女性仍远少于男性。这在银行业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2019年性别多元化统计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调查全球100多个国家在4个领域里的性别差距: 经济参与和机会、受教育程度、 健康 与生存、政治赋权。2019年12月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2019年,彻底消除性别差距所需的时间缩短为99.5年,比起2018年的108年略有进步。男性和女性难以在有生之年实现性别平等。2019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从政女性数量的大幅增加。然而,政治仍然是迄今为止进展最为缓慢的领域。男女在教育和 健康 领域已接近实现性别平等,而在经济参与领域,追求性别平等的努力面临巨大挑战。经济领域的性别差距有多种原因,包括担任管理或领导职位的女性比例长期偏低、工资停滞、劳动力参与度和收入水平低下等。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表示:“ 支持性别平等对于建立强大、团结和具有风险抵御力的 社会 至关重要 。 对于企业而言,性别多元化也必不可少,能够帮助他们展示利益相关者理念这一指导原则 。正因如此,世界经济论坛携手政商界利益相关者,共同加快行动,不断缩小性别差距。”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实施三大关键战略,才能稳步实现未来劳动力的性别平等:通过技能培训或再培训,确保女性掌握颠覆性技术;改善多元化招聘机制;以及打造包容性的职场文化。
自2011年以来中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的排名为: 2011年61名 ,2012年69名,2013年69名,2014年87名,2015年91名,2016年99名,2017年100名,2018年103名, 2019年106名 (共153个国家参与调查)。 中国这个排名居然持续下降,令人惊讶。 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一的是菲律宾(全世界16位),韩国排名108,日本排名121(比上年下降11位),是发达国家中的 倒数第一。
2019年,中国四大项指标的排名(排名是本国内两性之间的各项指标的比值,男女各项指标差距越小,排名越前):经济参与和机会排名91、受教育程度排名100、 健康 与生存排名153、政治赋权排名95。一些具体指标排名: 高等教育入学率排名第1,专业和技术工作者排名第1,劳动力参与率排名70,相近工作的工资平等排名75,立法者、高级官员和管理层排名125名,女性担任部长职务132名,出生性别比153名 。也就是说,在学校教育上中国女性完全不输男性,但越往上晋升女性和男性的差距越大,在男女平权指标上越拖后腿。中国这一排名的持续下降,似乎没有引起中国 社会 各界的重视。
桑德伯格就“为什么我们的女性领导者那么少”为题作TED演讲后收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她从自身经验体会到,“闭口不谈这个问题肯定会适得其反,阻碍自我发展”,“公开谈及这些问题能够促使变化的发生”。
桑德伯格说,“我们敢于去提起并讨论性别问题对女性的影响。我们不再假装性别偏见不存在,或是避开不谈。正如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实践所证明的, 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环境不仅能让各种组织和机构更好地运行,也会为所有人带来更大的幸福。 ”“只有当所有人都去反对那些阻碍女性进步的观念时,真正的平等才会实现。”中国,还需要对性别平等问题有更多的讨论和行动。
《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内容参考:
1.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
2.《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发布
杜嘉班纳事件怎么回事?
杜嘉班纳辱华的始末:
2018年 11月21日,Dolce Gabbana将在上海世博会中心举办第一届大型时装秀“The Great Show”,许多明星将受邀参加。与此同时,Dolce Gabbana在预热期间专门拍摄了一场名为“用筷子吃饭”的广告活动,该活动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意大利经典饮食相结合。
然而,这则广告引起了中国网民的不满。一些网民指出,电影中叙述者的“汉语发音”和语调,以及“中国模特”用筷子吃比萨饼和意大利甜面包卷,都涉嫌歧视中国传统文化。
尽管@Dolcgabbana在微博上删除了这段视频,但它仍然将它发布在即时新闻和Facebook账户上,这一“涉嫌侮辱中国”的事件在外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很多争议。
FACE book ? 创造人?
Facebook(非官方中文名称:脸书、面书或非试不可、非死不可)是一个社交网路服务网站,于2004年2月4日上线。从2006年9月到2007年9月间,该网站在全美网站中的排名由第60名上升至第7名。同时Facebook是美国排名第一的照片分享站点,每天上载八百五十万张照片。据报道,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6月25日在法国表示,Facebook的活跃用户数量将在明年某个时候达到10亿人。随着用户数量增加,Facebook的目标已经指向另外一个领域:互联网搜索。
网站对用户是免费的,其收入来自于广告。广告包括横幅广告和由商家赞助的小组(2006年4月,有消息称Facebook每周的收入超过一百五十万美 元)。用户建立自己的档案页,其
中包括照片和个人兴趣;用户之间可以进行公开或私下留言;用户还可以加入其他朋友的小组。用户详细的个人信息只有同一个社交网络(如学校或公司)的用户或被认证了的朋友才可以查看。 据TechCrunch(译者:硅谷最著名的IT新闻博客。)报道,“在Facebook覆盖的所有学校中,85%的学生有Facebook档案;(所有这些加入Facebook的学生中)60%每天都登陆Facebook,85%至少每周登陆一次,93%至少每个月一次。”据Facebooke 发言人ChrisHughes说,“用户平均每天在Facebook上花19分钟。”据新泽西州一家专门进行大学市场调研的公司“学生监听”在2006年进行的调研显示,Facebook在“本科生认为最in的事”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苹果的iPod,和啤酒与性并列。
创始人: Mark Zuckerberg 马克·扎克伯格 创始人
公司: FaceBook 脸谱网 成立日期: 2004年2月4日 资产结构: 由 Peter Thiel and Accel合伙人共同成立 雇员: 32个在帕拉阿图,4个在波士顿 总部: 帕拉阿图 马克·扎克伯格简介: 从外表上看,26岁的美国人马克·扎克伯格和刚刚走出校园的普通年轻人没什么不同。他穿简单的T恤、松垮的牛仔裤、阿迪达斯运动鞋,讲起话来甚至有点腼腆。四年前,扎克伯格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辍学生,而现在他已经成为互联网界的风云人物。作为社区网站Facebook的掌门人,《福布斯》日前评选出十位最年轻的亿万富翁,26岁的马克-扎克伯格以69亿美元的身价排在首位,他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 2010年09月24日上映的《社交网络》就是以马克·扎克伯格本人及其创始Facebook的经历为原型的电影) “盖茨第二” 扎克伯格的人生就像一个电影剧本。他从小就表现出超常的计算机天赋,6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编程。大学进入众人向往的哈佛,然后又毅然选择退学创业。不到4年的时间,Facebook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互联网的一个奇迹。目前它的用户数量已经突破3.5亿,而它的市值估计也已经高达300亿美元。 这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子被人称为“盖茨第二”。的确,他的人生和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在19 岁开始创业,同样是哈佛大学的辍学生,同样年纪轻轻就赢得世人的尊敬。 1984年5月,扎克伯格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富人区。他的父亲是一名牙医,母亲则是一位精神病医师。他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儿子,在4个孩子中排行老二。10 岁的时候,他得到第一台电脑,从此开始了一段奇妙的电脑人生。 扎克伯格自学成才,学会了编程。高中的时候,他为一款MP3播放器设计了插件,这个软件可以识别用户的收听习惯,自动创建符合用户口味的播放列表。扎克伯格把这款软件上传到互联网上供人免费下载,他的才华很快得到了一些大公司的赏识,包括美国在线和微软等大公司都向他抛来橄榄枝。但扎克伯格最终决定以学业为重,于是他来到哈佛。 黑客生涯 在哈佛,扎克伯格读的是心理学,不过他仍然痴迷于电脑。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扎克伯格就已经表现出创业者所需要的大胆、自信以及能干的特质。 正是在哈佛的宿舍里,扎克伯格写出了Facebook的网站程序,他甚至还在这里尝试了一下黑客生涯。当时哈佛大学不像其他学校那样提供附有学生照片和基本信息的花名册。扎克伯格想为学校建立一个网络版的花名册,但学校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相关信息。“我只是想证明这事可以办成,”扎克伯格说。于是这位哈佛大一新生在某个夜里入侵了学校电脑的数据库,获取了里面存储的学生照片。 扎克伯格把这些照片放在他自己设计的网站上,后来这些照片的点击量超过了2.2万次。校方对他的行为非常不满,给了他一个“留校察看”的处分。扎克伯格最后向他的校友表示道歉,尽管他一直认为自己没错。他说:“我只是认为这些信息应该是公开的。”
“黑客事件”后不久,扎克伯格与他的两个室友莫斯科维茨和休斯一同创建了Facebook网站。他们花了一个星期编写程序,把网站定位为哈佛校友的联系平台。2004年2月,Facebook正式对外推出,它立刻横扫哈佛校园。当月底,就有超过半数的哈佛本科生成为它的注册用户。两个月后,Facebook的影响力已经遍及所有常春藤院校和其他一些学校。截至2004年底,它的注册人数已经突破了100万。 后来扎克伯格选择从哈佛心理学系退学,专心营运Facebook网站。他在2006年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表示,促使他决定离开哈佛,是比尔·盖茨2004年在哈佛电脑课上的一席讲话。“盖茨鼓励我们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某个项目,而当时哈佛也允许学生休学创业。当时盖茨开玩笑对我们说‘如果微软失败,我会重返哈佛’。”没有犹豫太久,扎克伯格追随前辈的道路,也离开了校园。 娃娃CEO 2005年春天,扎克伯格为自己的网站争取到了一笔1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签完合同,扎克伯格从硅谷所在的帕洛·阿尔托开车前往伯克利,准备和朋友们庆祝一番。但他却在路上遭遇了人生当中一段惊心动魄的意外。 途中,扎克伯格在一个加油站下车准备给汽车加油。此时一名男子从旁边的树丛里跳出来,手里挥舞着一把枪,嘴里大声囔着什么。“他没说要什么,我想他可能是服用了毒品。”随后,扎克伯格退回到车里,毫发无伤地离开了现场。事后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我能活下来真是幸运。” 事实上,这段插曲就像扎克伯格的人生道路一样:前方充满未知,中间有曲折,但结果却好得出乎人的意料。 位于硅谷的Facebook总部更像是一间大宿舍。这里工作的400名员工可以免费享用食物和洗衣服务。他们很晚才出现在办公室,但在办公室待得也很晚,如果有派对的话则会走得更晚。 Facebook被人称赞为继Google之后出现的最伟大创意,但Facebook后面的那张年轻得还有些青涩的脸庞让人禁不住要问,这个23岁的年轻人是否足够成熟来驾驭一家公司。《华尔街日报》硅谷专栏作家斯威舍曾把扎克伯格称为“娃娃CEO”。当被问及扎克伯格是不是一个好的CEO时,斯威舍表示:“我不好说。我认为他还很年轻。” 但扎克伯格身边的人都说他很聪明,学东西很快。虽然这位20出头的CEO还穿着帽衫,也许不穿袜子,但他却在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和同龄人不同,23岁的扎克伯格像是一个战略思考者。 不过扎克伯格也会犯错。目前,Facebook主要靠广告和赞助盈利。去年,Facebook引进了“灯塔”项目,这个项目可以监测用户在购物网站的访问情况,并自动向用户的好友报告。用户们纷纷投诉认为这项功能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比如要是有用户在网上给他的妻子买了一枚钻戒想给她意外的惊喜,但由于“灯塔”功能早已将他的这项购物行为传播给了他的亲友,这位用户想要制造惊喜的愿望也就泡了汤。 一开始,扎克伯格对这些抱怨视而不见,直到Facebook的3家主要广告商也威胁退出,扎克伯格才做出回应。他发表声明向客户道歉:“在这个功能的建立上,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在
我们如何处理问题方面,我们犯的错误更多。”年轻的扎克伯格并不惧怕犯错,他在各种尝试中积累成功的经验。 扎克伯格的性格也影响了整个公司,使其与众不同。在新闻集团2005年以5.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MySpace后,雅虎公司曾出价10亿美元想要收购Facebook,但被拒绝。 几乎每个主要的互联网公司都曾试图收购Facebook,但扎克伯格一直不为所动。这个年轻人到底在等待什么?有人认为他在等待更诱人的报价,有人则认为这只是他的计划与众不同。对此,他表示:“我只是想建立一个长期的东西。其他事情都不是我关心的。” 直到去年10月,微软公司宣布投资2.4亿美元收购Facebook1.6%的股权。按这个价位计算,创建才3年多的Facebook市值一举超过150亿美元。至于外界关心的公司何时上市的问题,扎克伯格在日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Facebook在2008年上市的可能性不大。他说:“不可否认,上市将给Facebook带来重大变化。但如果你要问Facebook何时上市,我的回答是既可能两年后,也可能是三年后。” 住在小公寓 在大多数同龄人才刚刚迈出大学校园,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扎克伯格已经到达了一个别人难以逾越的高度。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他谈到自己如何看待压力。他说:“我看过对乔布斯(苹果公司总裁)的一次采访,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从事了这样的工作并且处于这样的位置,那你就必须非常非常喜欢你的这份工作,否则一切就没意义了’。” “做Facebook这件事情需要付出很多劳动,如果你不把这份工作当回事,或者认为它无足轻重,花这么多时间在它身上实在是不理智。但我却从中能够得到很多乐趣,因为我与一群志同道合的聪明人一起努力,我们来自不同背景,有过不同经历,思考方式也不同,但我们却创造出一个共同的东西。” 尽管身价已经上亿,但扎克伯格的生活仍然普通如同常人。他不买贵的衣服;他有一套一室一厅的小公寓,房间里有一张床垫,他就住在那里。他说自己曾在家里为一个女朋友下过厨,但结果很失败。 扎克伯格这样描述自己一天的生活:“我每天早上醒来,然后走路去上班,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大概有4个街区。到了办公室,我开始工作,和人见面,整天讨论各种事情。然后我又下班回家睡觉。我没有闹钟。”有传闻说,扎克伯格曾拒绝微软高层提出的约会,原因只是微软把见面时间定在了早上8点,而扎克伯格那会儿还起不了床。 在被问到他的年龄到底是一个优势还是劣势时,扎克伯格说:“可能是利弊兼有吧?我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年龄肯定会缺乏经验和阅历。但也有一些事情是我敢做的,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可能已经不能够敢做敢为。” Facebook是一个社会化网络站点。它于2004年2月4日上线。 Facebook的创始人是Mark Zuckerberg,毕业于Phillips Exeter Academy,并继承了Exeter的传统进入了哈佛大学。最初,网站的注册仅限于哈佛学院(译者注: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部)的学生。在之 后的两个月内,注册扩展到波士顿地区的其他高校(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波士顿大学 Boston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 MIT、特福茨大学 Tufts)以及罗切斯特大学 Rochester、斯坦福 Stanford、纽约大学 NYU、西北大学和所有的常春藤名校。第二年,很多其他学校也被加入进来。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大学后缀电子邮箱的人(如 .edu, 等)都可以注册。之后,在Facebook中也可以建立起高中和公司的社会化网络。而从2006年9月11日起,任何用户输入有效电子邮件地址和自己的年龄段,即可加入。用户可以选择加入一个或多个网络,比如中学的、公司的、或地区的。 据2007年7月数据,Facebook在所有以服务于大学生为主要业务的网站中,拥有最多的用户:三千四百万活跃用户(包括在非大学网络中的用 户)。从2006年9月到2007年9
月间,该网站在全美网站中的排名由第60名上升至第7名。同时Facebook是美国排名第一的照片分享站点,每天 上载八百五十万张照片。这甚至超过其他专门的照片分享站点,如Flickr。 网站的名字Facebook来自传统的纸质“花名册”。通常美国的大学和预科学校把这种印有学校社区所有成员的“花名册”发放给新来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帮助大家认识学校的其他成员。 在2008年的年初,Facebook 的全球访问量已经超过MySpace,成为全球第一大社区网站。 《时代》年度风云人物 Time(《时代》周刊)网站美国时间12月15日宣布,26岁的Facebook创始人兼CEO Mark Zuckerberg(马克·扎克伯格)当选2010年时代年度风云人物。这是一个值得软件技术人员记住的时刻,因为在时代年度风云人物的历史上,这应该是第一次将一位程序员出身的杰出人物因为自己的作品而当选。[1] 有社交障碍的天才 虽然一心创立开放的世界,但私底下扎克伯格却是个极为低调的人,他不喜欢也很少和媒体打交道。虽然应酬越来越多,但他其实并不是个很懂得社交的人。今年夏天的时候,在硅谷的电脑历史博物馆,扎克伯格应邀参加活动并发表演讲。在后台准备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你不怎么参加这种活动吧?”扎克伯格简短地说了一个“不”字,随后喝了口水,双眼放空,望向远处。
O(∩_∩)O~足够多了……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Facebook为什么要推出“新闻标签”?
如果从方便用户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在为你定制私人的新闻内容,但是如果从画嘞或者说偷窃隐私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可能就很容易定位,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性格,然后用于他们大数据的开发。就把你当做成了小白鼠。仅代表个人观点。